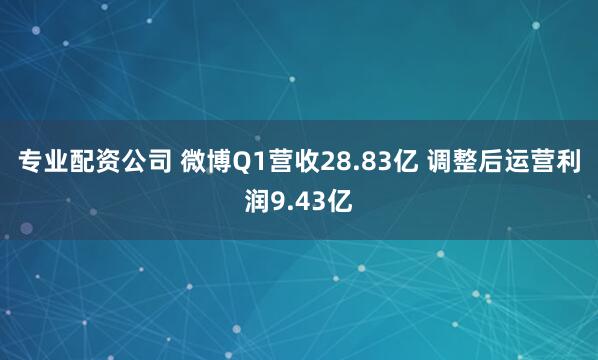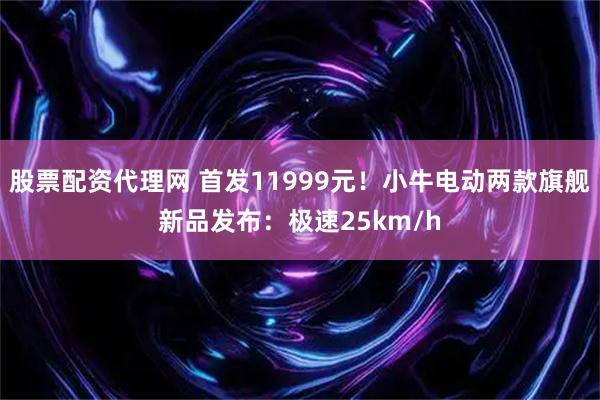在我小时候股票配资安全的平台,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说《毁灭》和《青年近卫军》是流传的文学名著。不少中国人不知道法捷耶夫死于自杀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我来说说。
《青年近卫军》是流传的文学名著
1956年5月13日,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、著有《毁灭》和《青年近卫军》的法捷耶夫在莫斯科近郊开枪自杀。他的死如一声震雷,划破了苏联文艺界的沉默。面对赫鲁晓夫“解冻”时期的风云突变,这位长期担任苏联文学“总管”的作家,终于以自毁的方式与过去诀别。他留下的遗书不仅是对党内文艺政策的控诉,更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深感幻灭的哀号。
从小干革命
法捷耶夫出身于一个激进家庭,自幼便受到布尔什维克思想熏陶。17岁入党,参加过远东游击队,与日军作战。革命履历成就了他“布尔什维克作家”的身份认同,也注定了他将文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。他自己曾说:“我首先是一个革命者,然后是作家。”他的处女作《毁灭》正是这一立场的体现,其高昂的斗争精神赢得了鲁迅的赞赏,被译为中文流传于中国左翼知识界。
展开剩余76%下图是苏联1971年发行的法捷耶夫纪念邮票。
苏联1971年发行的法捷耶夫纪念邮票
从文坛新星到“文学总管”
1920年代末,法捷耶夫加入了无产阶级文学团体“拉普”,并很快成为其核心人物。1932年,斯大林决定解散所有文学团体,改组为由党直接领导的作家协会,拉普多数成员反对,唯独法捷耶夫支持,遂被视为“背叛者”,但也因此获得斯大林的青睐。此后他成为苏联文学官僚体系的核心人物,1946年起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,直接执行斯大林对文艺界的整肃与控制。
在此期间,法捷耶夫以极大的忠诚贯彻斯大林的意志。他一面批判阿赫玛托娃、左琴科等“资产阶级倾向”作家,一面暗中接济他们,让他们通过翻译来谋生。他高调拥护日丹诺夫主义,却又在私下为受难者辩护。在“世界主义”批判运动中,大量犹太知识分子遭打压,法捷耶夫既是批判的主将,也是受命而行。他的“两面性”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深刻恐惧与妥协。
党性与良知的撕裂
《青年近卫军》的重写,是法捷耶夫文学生涯中的一道深深的伤痕。原作未突出“党对青年地下组织的领导作用”,遭斯大林痛批,《真理报》发文指责后,法捷耶夫被迫重写,直到1951年才完成。他明知这是对历史与文学真实的背叛,却不得不低头。他的姐姐曾回忆,这一过程使他几近崩溃。
类似的撕裂贯穿于他的整个“政治—文艺”生涯。他曾在私下承认:“我无权不相信总书记的话,但我知道那不是事实。”斯大林的信任将他推向高位,也将他的个人良知逼入死角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痛苦地说:“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。”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自我反思中发出的深切忏悔。
解冻后的幻灭与终结
1953年斯大林死后,法捷耶夫曾一度寄希望于赫鲁晓夫会对文艺政策进行改革。他写信上书,提出具体建议,要求见面讨论,但均遭冷遇。相反,赫鲁晓夫对他的清算不断升级,不仅撤职,还在文艺界放任对他的嘲讽与攻击。人们将过去的文学迫害都归咎于他,将他视为斯大林的“打手”和“棍子”。
1953年斯大林死后,法捷耶夫曾一度寄希望于赫鲁晓夫会对文艺政策进行改革
在身心俱疲之际,1956年5月13日,他开枪自尽,年仅54岁。他留下的遗书是对党文艺政策的最后抗议:“文学——这新制度的最高产物——已被玷污、戕害、扼杀。暴发户们在以列宁学说宣誓时他们的自负就已背离伟大的列宁学说……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,我极其愉快地摆脱这种生活,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、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。”
这封遗书被长期封存,最终于1990年代才在党报上公开。
悲剧人物的多重性
法捷耶夫既是严酷体制的执行者、“加害者”也是“受害者”,既充满权力欲,又有温情的一面;既“粉饰太平”,又在背后为朋友奔走呼告。他是斯大林主义文学制度的忠实代理人,却又以自杀的方式与之诀别。
他曾说:“当我总结自己的一生时,仍然不堪回首那些呵斥、告诫、训斥。”这种愧疚与羞耻,正是他人格中最复杂的部分。他既不如赫鲁晓夫所言那样“毫无党性”,也非作家们指控的“冷酷官僚”,而是一个被时代撕裂的人。
“被体制吞噬的灵魂”
英国史学家奥兰多·费吉斯评价他:“到底是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,还是做一个好人,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胜。”这句话准确点出了法捷耶夫悲剧的核心——一个本可成为伟大作家的灵魂,在斯大林体制的磨碾中碎裂了。
在极权体制下,忠诚者才安全股票配资安全的平台,而良知则自带危险。法捷耶夫在忠诚与良知之间挣扎,直到生命的尽头。他的死,是那个时代文学与政治悲剧的注脚。
发布于:上海市信誉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